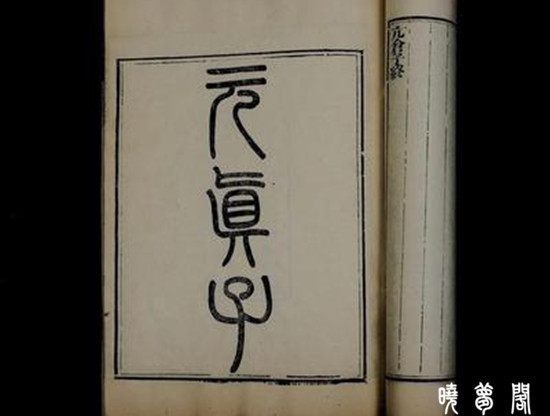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在这一时期制造了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鄂东惨案、确山(竹沟)惨案等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使国内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 的局面。 在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中,毛泽东特别关注平江惨案,以个人名义送牺牲烈士挽联,出席在延安召开的各界人士追悼“平江惨案”被害烈士大会,作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说,并警示全党要从中汲取教训,加强自身建设,主导了整个事件的善后。 什么因素促使毛泽东格外关注平江惨案? 在应对平江惨案的过程中又彰显了毛泽东怎样的政治智慧? 同时他又是如何借助这一事件破除中共党内顽固的左右倾思想,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 这些都是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问题,本文将要重点探讨。
一、毛泽东关注平江惨案的历史与现实因素
(一)平江惨案的缘起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对华政策也发生了转变,在军事上,日军基本上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将注意力
转移到打击日益壮大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上;在政治上,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 国际上,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避免同日本直接冲突,竭力缓和同日本的矛盾。 受此影响,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在 1938 年 12 月公开叛国投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逆转,国民党政策的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作出了“与共产党作积极斗争” 的决议,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 的方针。 会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 特别委员会”,并陆续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密件,转发饬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 此后,国民党策划了一系列反共摩擦活动, 而 平 江 惨 案 正 是 这 其 中 “ 最 严 重 的一个”。[1]152
1938 年 1 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 湘鄂赣地区的抗日游击支队,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 2 月 3 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奉命由平江嘉义出发,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为了及时安置和治疗在后方的伤病员、安排和保障抗日军人家属的生产与生活、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军、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交涉并争取释放政治犯,新四军军部决定在平江县嘉义镇设立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1939 年 4 月以后,为顾全大局,经新四军军部同意,留守处改为通讯处)。 中共湘鄂赣特委为领导湘鄂赣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将通讯处作为掩护机关,特委负责人涂正坤、黄耀南等以公开身份参加通讯处的工作。 湘鄂赣特委和通讯处成立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抗战的方针,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民族斗争,组织敌后游击武装,帮助抗日军属解决各种困难,解除前线将士的后顾之忧,并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行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对于湘鄂赣特委和通讯处工作人员的活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流言蜚语,污蔑通讯处人员不守法令,大肆活动,对国民不利,指责共产党不是真正的抗日,宣称要在平江肃清“共匪”。
平江惨案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国民党顽固派酝酿策划许久的。 蒋介石为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于 1939 年 1 月将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的部队从皖南前线调到他认为“共党活动最烈” 的湖南平江。 杨森原是四川的大军阀,移驻平江后,蒋介石命中统特务庄文炳到二十七集团军任政治部主任,对杨森进行拉拢,使其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命令。 杨森部随即开始了一系列策划取缔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的活动。 5 月 30 日,蒋介石发出绝密电报:“中共在平江嘉义岭一带大肆活动,其负责人为黄耀南、涂正坤,以游击为号召……查值兹抗战紧张之际,该黄、涂等竟于后方秘密活动,影响殊非浅鲜,请设法制止,以免滋蔓。”[2]117
6 月初,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召见杨森,杨森即迅速布置对新四军平江嘉义通讯处的“清剿”。 6 月 12 日,二十七集团军特务营营长何学植在杨森的指示下,调特务营二连长余启佑率兵包围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 下午 3 时左右,特务营中尉侦查员张绍奇以开会商量抗日有关事宜为名,将涂正坤骗离通讯处枪杀,后又将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乱枪打死。 当晚,国民党顽固派非法审讯通讯处罗梓铭(湘鄂赣特委书记、八路军少校副官)、曾金声(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新四军少校秘书)、吴贺泉(特委财务负责人)、赵绿吟(机要员、妇女干事)等四人,要求他们交出共产党名单,结果毫无所获,为了避人耳目,直至深夜零点左右,将这四人押离通讯处,前往嘉义镇附近的虎形岭,推入一个数丈深的淘金坑里予以活埋。 国民党顽固派以残忍的手段制造了这起“使前线将士愤慨,使后方同胞悲愤,使国际友人耻笑,使敌人汉奸快意”[3]122的惨案。
(二)历史与现实促使毛泽东关注平江惨案平江惨案是国共团结抗战以来蒋介石直接指使的一个比较大的摩擦事件。 蒋介石之所以对平江这一小地方如此在意,主要是因为平江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平江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一块心病,他们在这里鲜有胜绩。湘鄂赣地区的共产党是从平江发起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有平江团防参加;发动 30 万农军“二月扑城”是在平江;彭德怀、黄公略发动起义也在平江;围攻长沙是从平江发起,这次新四军留守处又设在平江。[3]39于是旧恨新仇一起迸发,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制造了这起令全国惊愤的惨案。 同样,领导过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建立过根据地的毛泽东对平江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早有认知,他关注发生在平江的惨案有其历史情愫和战略考量。
从现实来看,促使毛泽东关注平江惨案的因素主要在于:一是惨案发生在抗战的后方,指向的是英勇抗战的新四军,严重影响抗日将士的士气。 毛泽东曾悲愤地指出:惨案发生的地方“不是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4]575为对新四军等抗日将士及民众有个交代,毛泽东十分关注平江惨案。 正如惨案发生后《新中华报》社论所言:“当新四军自抗战以来转战
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收复沦陷的一部分失地,为国家民族英勇牺牲,名震全国。 不意新四军将士在前方血战方酣之时,而后方竟发生不幸事件,倘国法不予主犯及凶手以严惩,将何以告慰这些牺牲的先烈的英灵! 将何以告慰前方浴血抗战之新四军数百万英勇将士! 更何以公告我全国以民族国家为重,军事胜利第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各党派、各阶层群众。”[3]100二是惨案的发生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权威提出了挑战。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有一个过程。 中共党史著作一般都以遵义会议作为毛泽东全党领导地位确立的标志。 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领导地位一度受到自苏联回国的王明等人的挑战。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上,与毛泽东看法相对的是,王明等人认为,国民党掌握着全国的政权,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应由国民党来领导,共产党应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否则就会破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 而对于国民党可能与共产党决裂和向共产党进攻的问题,王明等人则认为,现在国民党实行全国抗战需要共产党的合作,是不会向共产党进攻的,因而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因此,他不仅自己不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还使部分党员和干部丧失了警惕。 惨案发生地平江的党组织原先为王明所领导的长江局所管辖,而后为项英所领导的东南局所管辖,由于受王明右倾思想的影响,党内有不少的人对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以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和认识。 1938 年 9 月,在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肯定中共路线正确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意见。[5]92 这使得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认可,毛泽东的思想也开始在全党特别是在王明原先所领导的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而平江惨案的发生无疑挑战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权威及影响力,自然为毛泽东所格外关注。
二、毛泽东主导平江惨案的善后
平江惨案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害怕中共追究责任,引起民众公愤,一方面制造种种借口,设法掩盖事实真相,推卸责任,另一方面,倒打一耙,对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加上“发展新组织”“诱惑群众”“破坏抗日”等“莫须有”的罪名。 由于国民党欲掩盖事实真相,严密封锁消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在 6 月 18 日离开重庆返延安商议解决各地摩擦事件的办法时,对平江惨案“尚一无所知”[3]67。 6 月 20 日后,十八集团军驻桂林通讯处才从平江逃出之新四军通讯处工作人员口中得悉概况。 到 6 月下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和中共中央才获悉平江惨案的消息。 毛泽东在了解惨案的经过后,不仅表达了个人的悲愤,还领导和组织全党对此事件做出有原则有力度的应对。
(一)理性分析事件原因,准确定性事件性质
早在平江惨案发生前,毛泽东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国民党内妥协摩擦的危险倾向在不断发展。 1939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对中共所面临的形势作了判断,认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 他指出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5]129。 6 月中旬,平江惨案详情还未报至中共中央南方局,但针对这一时期湖南乃至全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摩擦事件,周恩来就已经在南方局会议上提出在力争局势好转的同时,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正是由于有了精神上的准备,平江惨案发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才能从容应变,对此事件作出理性分析和判断。
关于平江惨案的原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作了深刻的分析:
从客观而言,主要在于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制造国共分裂。 毛泽东基于这一时期国内外形势,在延安“平江惨案”死难诸烈士追悼大会上指出,惨案的制造者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 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并认为《限制异党活 动 办 法》 是 顽 固 派 制 造 平 江 惨 案 的 “ 根源”[4]578。 而国民党顽固派之所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日军采取“以华制华”政策的影响,视日益壮大的新四军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正如张鼎丞在“平江惨案” 死难诸烈士追悼大会上对事件所作的分析:完全是反动派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配合日寇消灭新四军的举动。[3]109周恩来在得知事件后多次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查明惨案真相,并特意针对国民党最高当局转复薛岳电报中 “查涂正坤等纠结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官兵,灭尸缴械,危害地方”[6]64的说法据理力争,指出薛岳电报所述与平江惨案事实不符,是国民党当局有意在掩盖事实真相,认为“嘉义惨案,有其政治上之原因”[3]61。
从主观而言,国共合作抗日后中共党内存在右倾思想,疏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防范。 受党内右倾思想的影响,抗战初期,湘鄂赣特委就响应并提出了“中日矛盾为最主要,阶级矛盾为次要,毅然决然的转变政策,只求中国和平统一,一致抗日,对阶级斗争与土地革命的主张,是可以放弃的”[3]46“停止阶级斗争与土地革命,取消敌对阶级思想”[3]48“一切服从抗日”等主张,这些主张虽然对当时促进国共合作起了一定作用,但为了促进国共合作而失去原则,提出停止阶级斗争的主张是违背客观实际的。对此,中共中央曾派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处长李涛来平江予以纠正,但湘鄂赣特委仍有右倾思想残余。 涂正坤、罗梓铭、黄耀南等负责人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时,为不影响团结,一度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作了让步,这就更加助长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而这为平江惨案的发生埋下了隐患。董必武曾在分析事件原因时,沉痛指出涂、罗十余烈士“执行统一战线,相信当地政府,相信当地民众,相信驻扎当地友军,毫无戒备,竟遭余连抄袭至死”[7]361。 正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使得湘鄂赣特委负责人对顽固派缺乏必要的警惕,疏于对顽固派的防范。 平江惨案发生之前,同情中共的平江县新任县长余达美曾提醒涂正坤、黄耀南要注意杨森,且杨森曾派人到嘉义通知通讯处说:“新四军远在江浙作战,后方事宜谅以办妥,留守处没有保留之必要”[3]15。 对此,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虽有警惕,但仍有太平观念,对通讯处机关的安全未采取应有的防范措施,且情报工作薄弱,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情报,以致完全没有估计到顽固派会公开残杀通讯处人员。惨案发生之后,被调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的黄耀南在接受中共中央东南局就平江惨案的问题进行审查时,所作报告中指出:“湘鄂赣特委缺乏高度的政治警惕性,虽说对杨森的行为有所怀疑和警惕,但没有估计到事件出来得这么快。”[3]191中共中央东南局对此说法予以认同。 平江惨案的发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新四军平江通讯处采用了组织半公开的形式,将公开机关和秘密机关混在一起,差不多湘鄂赣边区的党政机关和军队,都知道通讯处是一个共产党机关,而这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
关于平江惨案的性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判定这是一起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摩擦事件。 毛泽东在延安“平江惨案”死难诸烈士追悼大会上指出:“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应该罚破坏抗日、团结、进步的汉奸和反动派,现在统一了没有呢? 没有。 平江惨案就是证据。”[4]576毛泽东把平江惨案看作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破坏统一的例证。 周恩来在惨案发生后致电陈诚时明确指出:“北事未平,南变又起,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 此种阴谋,弟敢断言绝非于反共,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3]53叶剑英在《论平江事件》中提到:某些顽固派的反共和汪精卫投降派的反共,实质上同是日本法西斯蒂的工具,葬送民族的掘墓人。[3]107董必武在定性平江惨案时,认为平江惨案是“一种有计划的、 有 步 骤 的、 大 规 模 的 破 坏 我 国 团 结 的 阴谋”[7]360,并对这一阴谋进行了深度剖析,认为平江惨案“不过千百摩擦事件中之一件,不过是最严重事件中的一件罢了”[7]361。 抗战相持阶段,全国各地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摩擦事件,平江惨案不简单是平江的个别问题,而是在国民党整个反共政策下顽固派有计划的反共阴谋,企图以局部的事变促成全国统一战线破裂。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平江惨案性质的判断,是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合理策略、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的重要依据。
(二)揭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坚持以合法斗争求团结
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初,为充实巩固统一战线,毛泽东就富有远见地指出: “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5]32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破坏统一战线,毛泽东领导全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第一 ,态度鲜明,要求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平江惨案发生后,周恩来等中共负责人相继致电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要求迅速查明事件真相,对凶犯给予严肃处理。 周恩来在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时称:“用特电请转呈委座,严令查明此案真象,对死者务请给以抚恤,对肇事者请严予惩治。 并责令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使中共党员得有生存之保障。”[3]53然国民党当局欲掩盖事实真相,对此事件采取了敷衍的态度。 对此,周恩来据理力争,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谎言和漏洞,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为壮大声势,1939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南门外体育场主持召开了延安党政军各界万余人参加的大会,沉痛追悼“平江惨案” 被害烈士,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均赶来参加此次大会。 毛泽东并以个人名义送牺牲烈士挽联:“日寇凭陵,困难方殷,枪口应当向外;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会场正中央悬挂着中共中央的挽联:“顽固分子,罪不容诛,挟成见,作内奸,专以残害爱国英雄为能事;共产党员,应该警惕,既坚决,又灵敏,乃是对付民族败类之方针。” 会上,毛泽东作了演说,强烈谴责 “平江惨案的那些刽子手,他们把进步分子杀了” ,“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4]577,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第二,把握大局,斗而不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枪口是对外,不是对内”,基于此,毛泽东告诫全党:“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5]129 平江惨案发生后,毛泽东这一思想在全党逐步得到认同并得以落实。 叶剑英在《论平江事件》中指出:“如果有人把现在所看见的一些反共的活动,看作是国共分裂的开始,这是不对的。 因为国民党绝大多数的同志,是拥护团结,要抗战到底的。”[7]359 第十八集团军驻湘通讯处同人在《悼涂正坤、罗梓铭等死难同志》中指出:“我们必须不避艰险的努力,使国共两党在任何挑拨离间的环境中,加紧亲密的合作,以打击挑拨者。”
平江惨案中暴露出来的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1939 年 8月 16 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党的工作路线时,毛泽东特意指出:关于党的工作路线,以浙江、广东、四川等省为好,原来的老苏区等区域党的工作路线转变较差,必须彻底转变。[5]135平江惨案发生时,湘鄂赣特委由于吸收大批新党员入党,忽视了党员的质量,一度出现变节者,给党组织造成了重大损失,教训是深刻的。 基于各地党组织发展新党员的教训,1939年 8 月 23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指出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趁机来进行破坏党的阴谋。 会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估计到党的组织的现状与目前环境,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1]181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级党组织将整顿、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工作的重点,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贯彻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清除党内异己分子、叛徒和投机自首分子等,在组织精简、党员审查以及工作方式的转变等方面都加大了工作力度,保存和巩固了党的力量。 10 月 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基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现实形势的分析特意提醒全党:“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 为达此目的,就要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坚决的斗争”[4]613,进而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任务,并把这个任务称为党的建设的“伟大的工程”。 10 月 10 日,毛泽东又提醒全党:“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我们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4]617
平江惨案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有组织的罪恶行为的开始”[1]181,事件如何善后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对六届六中全会确立的毛泽东领导地位也是一次重大的考验。 毛泽东领导全党通过有效举措把事件的危害降到最低,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做出了一些让步,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击国共共同的敌人,团结人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有效应对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提供了宝贵经验。 同时,通过惨案使全党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党内“左”、右倾思想的危害及其顽固性,为加强党的建设凝聚了共识,指明了方向。
(一)强化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权威和影响力
(三)指明了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
中共自建党起,就面临着与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作斗争的艰巨任务,这些“左”、右倾错误使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早在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就犯过右倾错误,从而使中共在国民党于 1927 年发动反革命政变时遭受重大的损失。 而后的三次“左” 倾错误又差点葬送中国革命。 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
又严重影响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危害着党的事业。 中共的历史表明: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容易犯右的错误,在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又容易犯“左”的错误。 毛泽东是在与党内错误思想不懈斗争中成长为党的领导人,他对党内错误思想有着天然的敏感性和斗争意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初,毛泽东就针对党内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是在对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对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它的要求,而不知同它的错误政策做斗争。”[5]32 而后为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做了很多工作,对克服党内错误思想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但党内错误思想有其顽固性,一有条件就冒出来祸害党的事业。 平江惨案的发生与当时党内有右倾思想残余、对国民党顽固派缺乏必要的警惕有很大的关联。平江惨案血的教训给中国共产党敲了警钟,毛泽东借此警示全党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加强自身建设,克服党内右倾错误,保持党员政治思想的正确性。 而1941 年发生的皖南事变又有党内“左”、右倾的影响和流毒。 这也表明克服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是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可等闲视之。 平江惨案发生后,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绝不是偶然的。 这也表明后来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是为了破除党内错误思想,加强党的建设,而不是所谓的与王明争夺党的最高权力。
[7]367“我们不害怕部分的逆流”,“不因某些顽固分子的仇视而减弱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坚强意志。我们中国已经有了独立统一的基础,我们努力巩固这一基础而发展之,以安慰我们的死难同志,以粉碎顽固分子的阴谋”。[3]1151939 年 8 月,中共江西省委通知湘鄂赣特委负责人黄耀南,要他顾全大局,停止武装活动,争取和平解决“平江惨案” 问题,巩固团结抗日。 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应对此事件时,以国共合作抗日为前提,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国民党顽固派,而对于国民党中拥护统一战线、拥护抗战的人则积极团结,将斗争性与统一性结合起来,磨而不裂,斗而不破。
第三,借助舆论和群众,争取民众支持。 惨案发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还善于利用《新华日报》《新中华报》等媒体来配合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占领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 惨案发生时,《新华日报》正处于被迫停止发行、与重庆其他九大报纸共同出版“联合版”之际,然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克服困难指导《新华日报》 通过出版“七七纪念特刊”、设法“抗检”和组织纪念专栏等形式[8]52揭露惨案真相。 1939 年 7 月 7 日和 8 日,《新华日报》接连两天在报纸上发悼念新四军平江惨案烈士的讣告《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同人哀告》,向国统区民众报道有关平江惨案的消息。 《新华日报》 总编辑吴克坚收集民众意见,号召舆论帮助中共中央正确解决此事件。 由于与国民党的多次交涉未见成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将抗议斗争升级。 7 月 1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 正式发表消息报道:《杨森部包围平江通讯处,杀害新四军人员》,公开点名肇事者。 7 月 31 日,周恩来在答《新中华报》记者问时,对此事作出了严重抗议:“杨总司令本人恐亦不愿承担此项考语,故我第二次致陈兼长官之电,不得不再度抗议,请雪沉冤,不达目的不止。 想最高当局,本大公无私之怀,必能平反此案,为死者伸冤,为生者保证其最低合法权利也。”[3]698 月 1日,《新中华报》发表《纪念“八一”,抗议平江惨案》社论。 8 月 13 日,《新华日报》复刊,第一版刊登叶剑英组织南方局军事组撰写的《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遇害烈士启事》,详细说明了平江惨案的事实,并在最后质问国民党:“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今则捕杀随意,无人敢问,国法何在? 军纪何存? 无法无纪,国何以立?”[3]89 中共中央通过舆论宣传,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响,使国民党顽固派受到舆论压力的巨大冲击,处于被动地位而不得不对事件作出回应。 9 月 13 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时针对包括平江惨案在内的各地摩擦 问 题 作 出 了 “ 近 来 情 况 比 较 好 一 点” 的评估。
三、历史评价
平江惨案发生后,其可能的危害性能够降到最低,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其重要的组织保障。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国内外的形势能够保持清醒的认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能够提前预见,并及时提醒全党。 惨案发生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大背景下,结合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的具体实情,对平江惨案进行理性分析和判断,借助舆论和群众,坚决抵制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的行为,坚持磨而不裂、斗而不破的原则,为共产党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又不致使国共合作破裂。 同时在组织上指导湘鄂赣特委进行调整,并对湘鄂赣特委和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在工作中存在的右倾问题给予纠正,使得湘鄂赣特委更加隐蔽精干,便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开展工作。 通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有组织有原则的应对,平江惨案得到了有效善后,毛泽东因此在全党也更加有权威和影响力。 平江惨案从反面教育了一度在国共合作抗日问题上挑战毛泽东权威的王明。 平江惨案的发生,也曾引起了王明对国民党的“震愤”[9],使他从与国民党只讲统一、不讲斗争的迷梦里逐渐醒悟过来,思想上发生了一些转变。[10]75王明思想的转变有利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全党的团结和统一。 受王明右倾思想影响较深的湘鄂赣特委、江西省委以及中共中央东南局通过平江惨案认识到自身工作存在的问题,更加以实际行动遵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指示,更加维护中央的权威。 1939 年 8 月 25 日,东南局、新四军负责人项英等人联名致电毛泽东等人就平江惨案的善后提出:“定九月十五在驻地开涂、罗追悼会,《抗敌报》出版【专】刊发表惨案经过、略传,已寄桂林。 特电告,并盼指示。”[11]627从致电可见毛泽东对东南局、新四军已有较大的影响力。
(二)发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顽策略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应对平江惨案的过程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始终贯穿其中。 正如当时十八集团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徐特立在追悼死难烈士时指出:“我们有大无畏的精神,对付阴谋家。 我们需要谨慎、缜密、忍耐的精神,分析事理,反对任何轻举妄动,治丝而纷的行为。”[7]371“必须正确解决‘平江惨案’,以巩固民族的团结和国共合作到底,才足以安慰死难者在天之灵!”[7]370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始终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前提,即使在原则性问题上进行斗争,也是适可而止,把握统一性与斗争性的统一。 坚定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 上 的, 任 何 共 产 党 员 不 许 超 过 自 卫 原 则”[4]590的态度,鲜明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4]591 的口号。 正是在平江惨案应对实践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善后工作才有序推进,不仅使国民党做出了部分让步,更为中共争得了舆论和道义上的支持,扩大了政治影响。 在其后的反共高潮中,毛泽东汲取平江惨案反摩擦实践中的经验,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收到显著成效,使“有理、有利、有节”反顽策略不断发展成熟。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九———一九四〇). 第十二册[M]. 北
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湖南省平江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 中国共产党平江历史
(1921—2003)[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3]平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平江惨案史料汇编[M].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
[4]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卷[M]. 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2013.
[6]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M].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6.
[7]中共湖南省平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平江革命历史文献
资料集[M]. 中共湖南省平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983 年版.
[8]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南方局与《 新华日报》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
[9]陈绍禹. 为死者要求雪冤[N]. 新中华报,1939 年 8 月 1 日,第
4 版.
[10]李堃. 关于王明评价的一些问题[J]. 高教研究,1989(2).
[11]项英军事文集[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