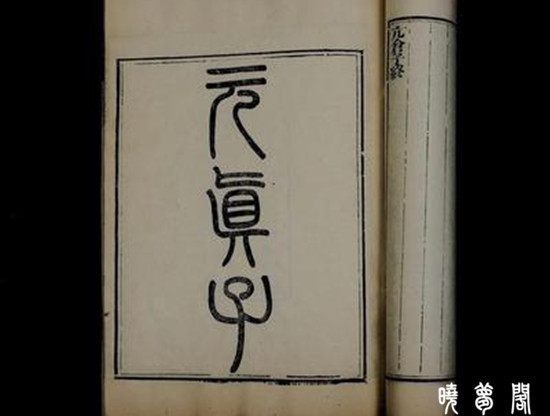宇汝松 1966年生,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服岭南,尚处瓯雒部落联盟的越南成为秦之象郡。公元前207年,亡秦将领赵佗据势割据为南越王,象郡成为南越国的交趾、九真二郡。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越南故地被分设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自此至968年丁部领建国“大瞿越”,越南始终以隶属北方中国的郡县形式而存在,此谓越南历史的“北属时期”或“郡县时代”。
崇尚巫鬼的符篆道教与越南本土信仰极为契合,越人自古就有信尚鬼神的习俗。《史记·封禅书》日:“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安南志原》卷二日:“交趾旧俗,信尚鬼神,淫祠最多。人有灾患,跳巫走觋,无所不至。信其所说,并皆允从。”①道教本是在巫鬼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王家柘认为:“张陵继承了巴蜀的妖巫鬼道,又革新之;于是巴人的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由巫鬼曜升为神仙,成为道教的主干。”②
道教与越人原始信仰的契合为道教南传越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随着中国政治机制在越南的有效建立,加之崇道循吏及高道术士的大力弘扬,初创不久的道教便南传越南。
张津此举似是对张鲁在汉中以“鬼道教民”,实现政教合一,“民夷便乐之”的模仿。《三国志·张鲁传》日:“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己信,号祭酒,各领部众,……民夷便乐之。”吕士朋指出:“张津在交州,好鬼神事,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道书,用以愚惑群众,其行径颇与黄巾及张鲁近似。”②王承文认为:“张津实际上是天师道信徒。其事迹与张鲁在汉中‘以鬼道教百姓’颇为相似。盖岭南瘴病交侵,生民夫横,故民多淫祀祈禳。张津遂仿‘二张’以鬼道的某些方式传教,使之不妄祀他神,以整饬社会风气。”③由此可知,道教始传越南约在2、3世纪初之交。作为汉廷遣派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张津倡行以道教佐治助化,企求实现政教合一,无疑为道教初传越南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和基础。
汉末道教初传越南除了上层路线外,还有广泛的民间渠道。道教创建之初在中原发展并不顺利。张角领导的准军事化之太平道,在184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失败后,遭到了彻底剿灭;五斗米道亦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被招降后分散肢解;神仙道士或以“妖妄”而惨遭诛杀,或“恐斯人之徒,’挟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④总之,整个道教在当时的发展跌人了历史低谷而日渐边缘化。加之汉末中原战乱连年,唯独远离政治中心的交州偏
安无扰,因此许多北方神仙道士南下避乱交州。
牟子曾以其亲身经历记录了这一概况:“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指出,不仅当时越南本地人对南下神仙道士所传的道教“多有学者”,而且对道教义理法术和神书典籍,如“王乔、赤松八仙之篆,神书百七十卷,长生之事”⑤,都颇为关注。此即表明,“在汉末原始道教创立后不久,神仙方术及神书(即《太平经》)、仙篆就已传到了交趾。”⑥道教初传越南已始见成效。
二、六朝期间道教入越的历史发展
六朝期间主要是指中国历史上的三国至南北朝时段。受张津政教合一、崇道助化思想的影响,此间镇守交趾的循吏大多善结道缘,一些饱学高道及道医术士亦亲临交州弘道布教,有力地推动了道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初具规模的民间道团组织的出现堪称是此间道教南传越南最为明显而又直接的发展成果。
(一)坐镇循吏的涉道史话
士燮(137_226)是继张津之后的交州太守。汉末三国时期,中原纷乱,民不聊生,而交州在士燮家族几代人的经营下,独能疆场无事,“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⑦,其中不乏著名的奉道世家和道医术士。
慕道仁厚,性好玄谈的许靖(约149—222)曾避难交州,为士燮“厚加敬待”。《三国志·蜀书·许靖传》日:“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靖身坐岸边,先载附从,疏亲悉发,乃从后去,当时见者莫不叹息。既至交陆,交陆太守士燮厚加敬待。……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陶弘景将其列人道教信徒的世系之中。《真诰·翼真检·真胄世谱》注日:“蜀司徒许靖,字文休,是长史六世族祖。”①长史即东晋时期道教上清派第三代宗师许谧(又名许长史),许氏是六朝时期著名的士族和奉道世家。
道医董奉游历交州时,曾以符水仙药使士燮起死回生,士燮亦因此与董奉交往甚密、深结道缘。葛洪《神仙传》日:
董奉者,字君异,侯官县人也。……杜(士)燮又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君异时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药内死人口中,令人举死人头摇而消之,食顷,燮开目动手足,颜色渐还,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后四日,乃能语。……燮既活,乃以君异起高楼于中庭。君异不饮食,唯啖脯枣,多少饮酒,一日三为君异设之。②
作为坐镇交州数十年、颇具郡望的太守,士燮交游高道,受用仙术,善结道缘,有力地推动了道教在交州的传播。交州当地人后来亦把士燮视为“士王”和“神仙”而立庙事奉。《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士王纪》日:“王器体宽厚,谦虚下士,国人爱之,皆呼日王。”“世传王既葬之后,至晋末凡百六十余年,林邑人人寇,掘发王冢,见其体面如生,大惧,乃复封瘗。土人以为神,立庙事之,号士王仙。盖其英气不朽,所以能为神也。”③
吴晋时期,陶氏家族曾数世担任交州刺史。《晋书·陶璜传》说:“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陶璜之子陶威亦被州人迎为刺史,陶威的弟弟陶淑、儿子陶绥也都担任过交州刺史。《陶璜传》说:“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陶氏乃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的先祖,亦为六朝时期名声显赫的奉道世家。《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说:陶弘景“七世祖溶,交州刺史璜之弟。”④陈寅恪认为,六朝期间的士大夫表面上儒道兼宗,而其世家“安身立命之秘,遗家训子之传”却是道教。陶氏家族世代乐守交州,主要与其世家内在的道教情怀有关,因为交州富产丹砂仙药,以及邻近滨海,宜为道教徒炼养和仙居。⑤
东晋末年,交州刺史杜慧度(373_423)崇尚老庄道学,颇具道者风范。《宋书·杜慧度传》日:“慧度布衣蔬食,俭约质素,能弹琴,颇好《庄》、《老》。”杜慧度崇道尚朴之雅趣一方面缘于六朝时期中原玄风对交州的影响,同时,作为一州之长,其崇道思想和风范亦必然会对州治时风产生重要的影响。黎正甫指出:“六朝中原风俗奢靡,文尚绮丽,交州士人也富于词藻,工于文章,而老庄之思想,清谈之风,也皆传人。……慧度交趾人,身为刺史,为一方之师表,而崇好老庄,求自然简朴之生活,其思想走入玄虚,盖受南朝玄学之影响,非儒家之风度。由其一人可以类推,普通士子,必更随风而靡矣。”⑥总之,崇道循吏的广结道缘、道风扇起,对道教南传越南无疑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二)高道术士的弘道活动
三国时,与道教关系密切的虞翻曾在交州广收门徒,训注、讲学《老子》十余年。虞翻(164_233),会稽余姚人,日南太守虞歆之子,“知医术”、“善治《易》”。其所治《易》善于利用道教丹经《周易参同契》的纳甲说、消息卦注解《易》理,形成了独异的道教风格。潘雨廷指出:
虞翻重视《参同契》中所发展的纳甲说及消息卦,用以注易,作为虞氏易组成部分之一。虞翻的易著,曾上呈献帝,且以示孔融,时约当建安十年(205)。上易表时有言:“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放发披鹿裘,布易六爻,挠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皆臣受命应当知经。”此所谓“尽吞三爻”及“易道在天,三爻足矣”之义,即指《参同契》中的纳甲。可见虞氏易与道教有密切关系。①
虞氏治《易》被赞为“东南之美者”,其易占祸福能“与神合契”,可见虞氏道术功法的不同寻常,以致孙权将其比作东方朔。历史上的东方朔亦主要因为其睿智和神异而常被神话为道教的神仙。李白曾赋诗云:“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②
东晋葛洪(283-343)出生于丹道世家,其从祖葛玄曾是三国时著名的炼丹术士。葛洪自幼十分喜好丹道仙学,其道术主要师承葛玄弟子郑隐,同时亦受其“博究仙道”的岳父鲍玄影响。葛洪因早年平贼旧功,50岁左右再被举荐大任。但葛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以炼丹服食
以延寿,听闻交趾富产丹砂而贱求苟漏令。越南史学家陶维英说:苟漏位于“宁平省安庆县地区和南定省丰盈县、义县。晋时,道家葛洪闻交耻有丹(丹沙用以炼仙丹),求补苟漏县令。在现今安谟地区,过去称为九真山的石山中有许多山洞,其中著名的如蝙蝠洞、徐试洞,葛洪确有可能想来这里找地方炼丹。”③
陈国符认为:葛洪“光熙元年(306年,24岁),往广州,遂停南土,当由日南(即今越南之顺化一带)往扶南(扶南国即今柬埔寨与越南极南部分)(其后因所闻见,记晋代南洋产砂之国,附于《太清金液神丹经》之后。)后返里。”④陈说肯定了葛洪造访越南,且是在24岁左右。但从该经所附葛洪的自述来看,此说与史稍有不符。《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载《抱朴子序述》日:
在此序述中,葛洪讲述自己年少就有游外学道的志向,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此即葛洪所言的“宿情”。葛洪之所以要远赴苟漏贱任“小县之爵”,主要因为当地“导仙服食之药、长生所保之石,无求不有”,其赴任苟漏令当是在他“年已及西”,“顾死将切近”之时,而不是陈说的24岁之时。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希望通过服食丹液延年遐寿、“荏苒止足”,“永辞坟柏”。
作为东晋著名的道士、道医兼道教学者,葛洪在赴任越南期间,一方面通过亲身搜访和实地考辨,详细记载了当地富产的仙丹灵药,并对它们“混杂无亲,妙物不显”的乱象,进行了“眼校”,使其良莠可辨,症药分明。从而为丹道、医道等“将来君子,各搜德业,不以管穴别
意,有所导引也。”①冯汉镛指出:
南齐时,阴铿妻子游历交州时,因当地地气卑湿而不幸患上了腹胀病,难以医治,濒临绝境,后遇苍梧道士林胜值此行医采药,以“温白丸”为其治愈疾病,化险为夷。④由此可见道医当时的精湛医技以及出没越地的频繁活动。总之,在当时尚处蛮荒的交州,高道术士,尤其是董奉、葛洪等道医在越地弘道布教,客观上推动了道教南传越南的普及和发展。
(三)民间道团的组织活动
六朝期间,南传越南的道教还出现了民间信众有组织的群起性活动。东晋末年,世奉五斗米道的孙恩因叔父孙泰被司马道子所杀,以“长生人”为号召聚徒起义,志欲复仇。孙恩败亡后,余众复推举其妹夫卢循继任统帅。义熙七年(411),卢循领导的信道义军从东南沿海转战至广州、合浦、交州等地,这些地方曾经都是孙泰任职郁林太守期间,大事传播道教的南越地区(包括当时的越南),信众基础较好。卢循义军进攻交州龙编(今河内东)时,李脱等组织当地信众积极响应。《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晋纪》三十八日:“循袭破合浦,径向交州;慧度帅州府文武拒循于石碲,破之。循余众犹三千人,李逊余党李脱等结集俚獠五千余人以应循。”
李脱之所以率众响应卢循进攻龙编,因为“李脱可能也是民间道教的信徒。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各地有崇奉仙人‘李八百’的民间道团(即李家道)活动,其首领常化名李脱或李弘(或作李洪),逛惑信徒和蛮族民众反抗朝廷,被称为‘左道’或‘妖贼’。……上述交州的李脱可能也是民间道教的一位首领,因其信仰与五斗米道相近,因此才结集当地蛮族应接卢循。”⑤王承文亦认为:“此‘李脱’即是被葛洪、寇谦之斥为‘妖道’的李家道象征”。⑥
李脱结集信众五千余人以应接同道卢循的起义,说明六朝时期越南民间道团业已形成且初具规模。虽然此次道教义军的首领纷纷殉道就义,起义失败,但道教组织的影响和发展并不会因此而止步,越南道团亦会在李脱之后获得持续更大的发展。据《宋书·褚叔度传》记载:“义熙八年(412),卢循余党刘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真,杀太守杜章民,慧度讨平之。”随着起义的失败,信众的四处溃散,道教在越南的传播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
隋朝存国时间不长,道教南传越南的史料十分有限。越南现存最早的石碑记载了当时九真太守黎谷崇道践教的有关史迹,可视为此间道教在越南活动状况的缩影。
据此可知,隋朝时,符篆道教在交州越南始呈兴盛,作为九真军政首长的黎谷不仅深谙道术、钟情风水,而且还热衷于修建道场,崇道修教,深得时人的认同和称颂。黎谷的事迹后来还被广传为神迹,当地人视之为福神,广泛建祠祭祀。如今的清化仍然可见百余座纪念黎谷的祠庙,由此可见黎谷当时的影响之甚。黎谷雅尚道教的行为必然会推动道教在当时九真地区的广泛传播。
(二)唐朝入越都护崇道史考
9世纪时,符篆道教在越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安南纪要》记载,唐穆宗时,安南都护李元嘉以府治门前有逆水(江水倒流),而担心州人多出反叛,因此之故,于长庆四年(824)派风水先生精心选址,于苏沥江畔新建小城以备府治迁新。以自然现象,尤其是反常的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发生神秘关联,是道教符谶常见的现象。李元嘉因逆水现象而奏移府治,一方面表明符篆道教已为当时大多数安南人所熟悉和认可;另一方面亦表明道教的符谶、风水、压胜等方术,已经开始深入影响当时的安南社会。李元嘉依风水所建的新城就是今天河内的初始城区。
咸通七年(866),雅尚仙道法术的高骈任静海军节度使,镇守安南,大力践传道教,道教在越南的传播由此而日至鼎盛。
知,高骈所作之法实为道教的雷法。许永璋亦认为:“似乎劈开巨石,是高骈施展法术呼唤天雷所致。”“这些具有神话色彩的记载,反映出当时道教的确很盛行。”②
最后,高骈施行道术符咒压胜安南王气龙脉及山精地灵。压胜又称厌胜,是道教常用的一种巫道法术。《中国道教基础知识》释“厌胜法”云:“道教中设置一些含有吉祥性或特殊意义的物品来镇邪驱魔,保护生灵不受损害。”③《岭南摭怪·苏沥江传》日:
《岭南摭怪·伞圆山传》还载高骈曾压胜山精灵气:
隋唐期间,南传道教在交州越南臻至鼎盛首先表现为广修道观,以致州内名观林立。道观是道教发展历史的物化记忆,唐代越南道观的建设成为道教南传越南辉煌发展的历史见证。唐代帝王优宠道教,曾多次诏令天下诸州广置道观。如乾封元年(666),高宗下诏“天下诸州置观、寺一所。”①永淳二年(683),“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②陶维英在《越南历代疆域》中指出:唐在越地所辖州郡主要有横山以北十二州和横山以南两个羁縻州。③据此可以乐观估计:唐高宗时,安南平均以中州计数,所置道观至少亦有24所以上。中宗复位以后,神龙元年(705)二月,令天下诸州各立中兴观一所。④如果不考虑民间自发修观,仅政府敕修的道观就呈自然增加之势。据《安南志原》卷二《交州八县记》记载,当时安南共有名观21所。载名史册的名观有峰州地区的白鹤通圣观,河内的玄天观(p等。
唐朝还曾大肆崇尚老子,把道教经典定为明经取士的主要内容之一,令王公百僚皆习,贡举人皆通。高宗上元元年(674)十二月,拟定“王公百僚皆习《老子》,每岁明经一准《孝经》、《论语》例试于有司。”⑥仪凤三年(公元678年)五月,诏令“自今已后,《道德经》并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⑦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七月敕令:岭南学子“有词理兼通、才堪理务者,亦任北选,及授北官。”⑧唐王室的一系列崇道举措为安南文人士子习道入仕提供了契机;强化和促进了道教在越南知识阶层的广泛传播,提升了越南道教信众的文化素质;亦为道教储备了大量有生的后备力量,爱州人姜公辅晚年弃政从道,堪称其中的典型代表。
姜公辅是唐时入仕京都的越南士子。《新唐书·姜公辅传》日:“姜公辅,爱州日南人。第进士,补校书郎,以制策异等授右拾遗,为翰林学士。”后又迁至“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任宰相不久,因犯颜直道最终导致德宗的不悦,而“请为道士”,深隐泉州南安县
九日山十余年。由此可见道教对当时越南文人士子价值观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由此可知,7世纪中期,阮常明在峰州修建白鹤通圣观,除供奉道教三清神像外,还接纳白鹤地
方神灵土令,并对其进行敕封。这是道教与越南本土信仰日趋结合而不断越南化的重要表现。
《越南历史》指出:“通圣观也供奉三江神(白鹤地区的福神)。这证明那个时期的道教和我们祖
先供奉山、河等神的传统结合起来了。”②
唐朝时,道教城隍神经过不断加封而成为越南地方普遍信仰的神灵。这是道教与越南本土信仰进一步融合的又一突出表现。“城隍”观念源于中国道教,本意是指防守城池的护城河,后来引申为保境安民的地方守护神。唐代时,城隍神信仰已成普遍的习俗,以致“水旱疾疫必祷焉”。③城隍信仰传人越南后,逐渐发展成为越南民间最为重要、普遍的信仰。韦凡州认为:
①王卡:《越南访道研究报告》,《中国道教》,1998年第2期。
②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第131页。
③《全唐文》,第5册,第4461页。
④韦凡州:《越南人信仰中的中越共同神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2页。
⑤[越]阮志坚:《越南的传统文化与民俗》,郑筱筠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