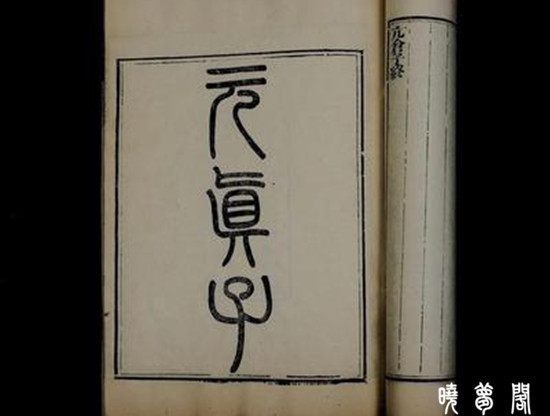在步入文明社会的漫漫征途中,中华民族选择了继承原始氏族的血缘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成长起来的是家庭与民族两大伦理实体,二者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伦理原理互为投射,形成了“人伦本于天伦”的运行原理。而伦理原理必然落实到道德个体身上,通过性善的人性假设和外在的道德规范,使道德个体成为社会所认可的孝子贤孙。当然,这种认可是通过精神和物质上的“得”而转化为现实的。由父子血缘的伦理关系经过一系列的伦理原理、道德法则、行为规范落实到个体,使其内化成为孝子并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现实性,这就是儒家“孝”伦理所形成的逻辑运行路径。
由“伦”至“理”的逻辑路径
儒家“孝”伦理由“伦”至“理”的过程是从“伦”的价值始源开始的,它通过“人伦本于天伦”的人伦关系运作原理,建构了以孝为本的伦理实体模式。由“伦”至“理”的逻辑运行路径蕴含着对儒家“孝”伦理的根源本性、伦理原理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究,其有三个特性:“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并以此为范型来建构人伦关系和伦理秩序;具有先验的乃至不证自明的伦理性和价值性,以家族血缘为元伦理和元价值;具有自我建构的功能,不仅以家庭自然伦理为根基,而且从中推衍、生长出社会伦理。”
在中国传统社会,五大伦理关系以血缘为轴心而衍生,这就是最基本的“伦”。“伦”由血缘的自然情感发展成为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情感,既具有无可辩驳的神圣性,又具有最现实的社会生活基础,就像父子之伦源于血缘亲亲,既具有自然天性又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在儒家“孝”伦理的逻辑运行过程中,“伦”以父子血缘关系为根基和范型来展开伦理内容,血缘关系既是其理论架构的逻辑始发点同时又是伦理建构的深厚基础。儒家就是用这种自然的血缘关系来建构父子人伦关系的。父子关系并非任由我们的意志选择,它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生活环境。父子血缘关系对处于其中的个体来说就是他的“自然伦理”,因为父子血缘关系的存在先于个体生命的存在。所以,父子血缘关系是由它的生物性所决定的,个体无法选择也不可能人为更改。血缘关系的天然性促成了它的神圣性,这是伦理价值的最后根据,并且自然而然、毋须反思。所谓“见父自然知孝”,就是这一血缘情感的价值逻辑。②
但是,仅有自然的父子血缘关系是不够的,进入文明社会如何给这种血缘关系以合理的伦理定位,使之按照伦理的原理良序运行,需要人类用智慧加以解决,这就是由“伦”向“理”的逻辑运行过程。对此,儒家“孝”伦理以父子血缘为核心确立了“人伦本于天伦”的人伦原理。五伦之中,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是天伦,君臣关系本于父子关系而建,朋友关系本于兄弟关系而立,由此建立中国传统社会人伦关系的基本原理:“人伦本于天伦”。人伦原理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性和秩序性的原理,因为血缘关系使个体在家族中具有天然的长幼之序,其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五伦秩序,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曼),这正是儒家“孝”伦理理想的伦理秩序。
以“人伦本于天伦”为伦理原理建构伦理实体,儒家“孝”伦理始终秉持着血缘——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模式,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建构了三种以孝为本的伦理实体模型:以孔孟为代表的“父慈子孝”的生态互动模式;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父为子纲”的父权意识模式;以程朱为代表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父权专制模式。第一种是充满人性的,第二种则具有强权意识,第三种则具有专制性质。
“父慈子孝”的生态互动模式之特点在于,强调伦理主体履行伦理义务之双向性与对等性,因此要求伦理行为的双方都要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并尽可能地把这一伦理过程导向善的理想价值状态。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这样几种情况:一是父慈子孝,这是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先秦时期对父子双方都提出了相应的道德要求:“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④;“请问为人父?日:‘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日:‘敬爱而致恭…⑤。可见先秦时期,对于父子的道德要求是双向的,甚至还认为在“父慈”与“子孝”之间,“父慈”是首要的,强调父母的道德示范作用,这种父子关系对于道德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和谐与有序都是至为关键的。⑨二是父慈、子不孝或者父不慈、子孝,二者在互动中没有按照回报的原理采取伦理行为,并未达到彼此的预想状态;三是父不慈、子不孝,这种状况主要是春秋战国混乱时期出现的臣弑君、子弑父的情形,此时已处于伦理失序、道德失范的社会状态,是一种伦理的恶性互动。为了规避这种恶性循环,保证在上者的权益,日后董仲舒提出了“父为子纲”的父权意识模式。“父为子纲”的父权意识模式要求确保双方伦理关系的相对稳定性,要求其中一方能够单向地恪守本分,履行自己的伦理责任,道德行为不以对方为转移,以免陷入相对的循环之中。应该说,它在维护人伦关系和稳定社会纲常方面,比“父
慈子孝”的生态互动模式更有力量。如果说“父慈子孝”的生态互动模式强调天然的血亲情感,则“父为子纲”的父权意识模式更注重宗法等级的秩序性,从此双向的父子关系变成了单向的父权模式。但不管怎样,董仲舒“父为子纲”的父权意识模式还只是讲究尊卑等级,及至程朱宋明理学时期发展为“父要子亡,子不碍不亡”的情况,就成了绝对的支配与强权。随着理学的长期宣传和倡导,宋明以来“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和“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等观念日益占据上风。现实生活中,父权专制也进一步强化,子辈的地位更加低下,导致各种愚孝层出不穷,最终天理人欲的礼教变成“杀人”、“吃人”的工具。造成这种极端情形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父权专制模式被神圣化和绝对化。当然,这对于稳定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言,其作用和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由“道”至“德”的逻辑路径
儒家“孝”伦理由“道”至“德”的逻辑路径表现为:从性善认同的“道”之法则出发构建“德”的价值规范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孝为本的道德自我。关于道德的人性起点,中西方道德哲学采取了不同的认知路径:一个注重通过日用情感的生活体验来感知人性,一个重视通过纯粹理性的哲学思辨来把握人性。对此,儒家“孝”伦理认为人性是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的探究和把握,而对于人性的把握最恰当之处就是把人放在当下的伦理情境中去感受和认知他的道德取舍,进而判断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之处。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家族血缘特性使得儒家“孝”伦理把血缘价值看得高于一切,并以血缘关系为基点进行推己及人的伦理推断,相信每个普通人成圣成贤的道德可能,并由此构建人性向善的伦理假设。当然,不可否认,性善和性恶共同构成儒家人性问题的一体两面,但是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性善论。性善向人们昭示人类过一种道德生活的可能性,性恶则指出在通往道德生活的过程中我们还有继续努力的必要性。如果说,“血缘”是儒家“孝”伦理关于伦理实体的根本性价值理念,那么“性善”就是儒家“孝”伦理关于道德自我的根本性价值理念。
在性善信念的指引下,儒家“孝”伦理以孟子的德性论为基础提出,道德规范不应该是对人性的束缚,相反应该是对人的德性的造就。如何造就呢?具体来说,在儒家“孝”伦理的价值规范体系中,对个体“德”的造就分为三个层次:“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首先,始于事亲。如何事亲呢?曾子日:“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⑧这里孝分为三个等级,最基本的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侍奉照顾,也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来赡养父母;第二等级的孝就是自己的行为遵守仁义,不给自己和父母招来灾祸,从而使父母免受屈辱;第三等级的孝是通过建功立业给父母增光添彩、荣耀宗亲。孝非外烁我也,而是源于对父母的爱敬之情,正是这种情感促使孝子通过自身的德行修养以及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被广泛认可,从而光耀宗亲、显赫门庭。正如台湾学者韦政通所说:“这样一个充满家族意识的社会中,人生自然会以光宗耀祖、兴家立业、衣锦还乡为最高的荣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生价值的表现,不在忠,便在孝。”⑨
其次,中于事君。所谓的“事君”实际上讲的就是对国家尽忠。在这里,光耀宗亲之孝成为报效国家的原动力,孝从原初的“善事父母”上升为对国家的忠孝,从最原始、朴素的血缘之情上升为报国为民的大爱。最明确地将孝与国家相联系的就是《吕氏春秋》所讲的“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不罢北”∞。君主履行孝道,既能使臣下俯首听命,又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臣下履行孝道,必然能忠于君主,为官清廉,危难之中从容赴死;百姓履行孝道,必然勤于耕耘并在战争中固守阵地,慷慨赴死。虽然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不同阶层守孝结果的揭示,但却给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从孝的基本内涵出发,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忠于自己的孝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报效祖国、回馈社会,这种孝已经超越了血缘的界限而走向更高的社会责任。
最后,终于立身。儒家向来注重“立身”,由“立身”之孝而引发对民族、天下的道德责任。如何“立身”,《大学》有明示:“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立身”的关键是“身修”,因为“身修”是连接前后的枢纽,而“身修”的最终目的是“天下平”。由孝而至立身,由立身而引发出修身,由修身而达致天下平,逐步连接起了血缘亲亲之情与民族天下的关系。此时,孝已经从单纯的血缘之情升华为对民族的大爱、大孝。正如潘光旦先生在《论“对民族行其大孝”》@一文中所揭示的:能够为了民族的一切奉献自己生命的人,他们通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仁义行为成为民族的楷模、时代的英雄,并且不仅为本民族而且为世界所敬仰,树立了本民族的光辉典范,这样的人是对民族履行了大孝的人。
儒家“孝”伦理通过这一价值规范体系的建设,促成了以孝为本的道德自我建构,从而形成个体内在的孝德品质。在这一过程中,儒家以孝为本的道德自我建构遵循了道德发展的逻辑规律,呈现出递进的三个层次:首先,儒家“孝”伦理在中国传统入性论的基础上,设定了人性本善,认同每个个体都有向善并成为孝子的可能性;其次,在道德规范中从多种渠道对人们进行孝的道德教育,不仅家庭、家族氛围中充斥了大量孝的习俗、风俗,而且社会大力倡导、学校循循善诱,整个生活环境都充斥着对儒家“孝”伦理的宣扬;最后,由对父母天然的爱敬之情和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认同、践履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所期望的孝子。人性自我——规范自我——道德自我,层层深人、环环相扣,由此形成儒家以孝为本的道德自我建构的辩证结构。儒家以孝为本的道德自我建构的意义就在于,使人们从内心深处认同儒家的“孝”伦理,从两形成具有自主孝意识的主体人格。
由“德”至“得”的逻辑路径
道德追求的是什么?难道是生活在理念世界里的虚无?显然不是。道德的本质不是远离“得”,而是要学会如何在处理现实复杂利益关系中获得正当性;道德的完满也不是不要“得”,而是能够自如地运用符合“德”的方式去“得”。儒家“孝”伦理发展到“德”的阶段,便在个体自身内部完成了“孝”的内化,但这只是抽象地、理论化地完成。儒家“孝”伦理的意义与价值,决不仅仅是精神的自我完成,而是“外化为他物”,这种现实地外化就是“得”,就是使儒家“孝”伦理能够更有效地干预现实社会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外化为他物”也即“得”,就是儒家“孝”伦理逻辑运行的目的。
在儒家“孝”伦理看来,与“德”相比,“得”是伦理理念中的生活世界,具有直接的世俗性。尽管如此,“得”的实现与获取也不能偏离伦理的逻辑和轨道。那么,如何能够实现“德”与“得”相连呢?这就是“德者,得也”——儒家“孝”伦理的最终目标。“德”与“得”相通,实现了儒家“孝”伦理的伦理精神与社会现实的融合贯通,达到了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那么,如何能够由“德”至“得”,“德”如何能够“得”,这就成为儒家“孝”伦理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儒家“孝”伦理中,“德”与“得”互相投射,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逻辑结构。第一,“得”必须有“德”。在中国传统社会,因为孝行而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孝子不乏其入,这种认可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嘉奖:在物质上能够获得上层的封赏,比如对孝子实行赦免赋税的优惠等;在精神上获得社会的广泛赞誉,孝子们被旌表门间、载入史书,甚而能够因为孝行被选人官。例如:“以荐举方式直接录用授职地方长官或按朝廷统一规定的量化指标‘计口察举孝廉’,或不受名额限制把本辖区孝悌之人不定期随时表荐上奏,由朝廷直接授予官职,这是历代封建王朝最为常见的以孝选官方式。此外,以家庭或家族为单
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授职赐官于孝子,也是以孝选官的典型事例。”@反之,如果有不孝者,则被除名削爵,永世不得续用。上层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宣扬营造了浓郁的重孝氛围,使“得”必须以有“孝德”为前提。
第二,“德”必然能“得”。《中庸》援引孔子的话:“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诗》日:‘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舜因何能贵为天子,因为舜是大孝之人,德行高远,所以富有四海,尊为天子。而且这种大德能使老百姓受益,自然就会受到上天的保佑,所以大德之人必然会“得”。这里朴素地表达了“德”不以“得”为目的,但“德”却必然能“得”的善恶报应思想。父子是血亲相连的天伦关系,如果孝敬双亲是为了赢得孝子的美名和求得功利,则损害了亲亲之情,使人失去最基本的情感依托和精神家园。所以,“得”并非最终目的,只是在进行价值预设时,人们确信孝子必然会得到好的归宿;在运行机制的安排上,良序运行的社会必会给予孝子应有的报偿。所以,在主观动机上,“德”并非为了“得”;但在客观效果上,“德”却必然“得”。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安排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在官员的任用和提拔上还是在社会现实利益的分配上,对于孝子都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
第三,有“德”就是“得”。孝的根本是对父母的血缘情感的真实流露,而不是出于机心和利益,那种对自然本真的背离会导致孝的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特别是汉代以来,越来越多外在的物质利益和功名利禄附加在孝上面,使孝越来越远离人性的自然。而孝本该是为人子女良善本性的流露和自然天性的表达,有父母可以供养就是福气,就是大“得”。这里有一段文惠太子与临川I王之间关于孝的对话,临川王认为,“孝为德本,常是所疑。德施万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岂因积习?”文惠太子日:“不因积习而至,所以可为德本。”可见,孝是德之母本,是道德的始源,是源自人的真性情,不因积习而至。这种发自内心的
亲爱父母之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念和追思,是儒家“孝”伦理深刻的情感基础。这里,人们是为了孝敬父母而孝敬父母,不掺杂任何外在的功利目的。
第四,“德”的目的是为了“得”。此时,孝敬父母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是通过所谓的孝,使自己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回报,甚至是通向政治成功的阶梯。践履孝仅仅是为了响应上层统治者的号召,被上层统治者认可,被普通民众接受。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孝”伦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具有很大的实用性。这就牵涉到真孝与伪孝的问题。那种行为虽严守礼仪规范,然而却表里不一的人是真孝吗?那种只讲究名教的礼俗,甚而沽名钓誉以求取官职的人是真孝吗?这只是装模作样,虚情假意的伪孝。伪孝者假借孝之名谋取个人名利,为了“得”而“德”,体现了其道德上的虚伪性。
可以看出,前三点是儒家“孝”伦理由“德”至“得”逻辑运行的正向价值体现,第四点则是其反面。社会生活中第四种情况确实存在,无法回避,但应从制度设计和安排上尽量避免,由此形成儒家“孝”伦理现实而有机的生态,并真正深入社会,发挥其导向作用。
至此,我们可以对儒家“孝”伦理的逻辑运行路径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由“伦”至“理”的逻辑运行过程是从客观的亲子血缘关系出发,进而推出“人伦本于天伦”的人伦之理,这实际上就是以孝为本的伦理实体建构过程;由“道”至“德”的逻辑运行过程是从人的善性良心出发建构孝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并内化为个体内在的孝德的过程,也就是以孝为本的道德自我建构过程;由“德”至“得”的逻辑运行过程解决的是孝德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得失问题,也即儒家“孝”伦理的现实外
化过程。由此,儒家“孝”伦理逐步形成由现实的亲子血缘关系出发,最后又回归现实生活的逻辑运行路径。
①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6的,第26—29页。
②参见拙作《“伦”与“孝”价值同一性的道德哲学解读》,《华中
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③《论语·颜渊》。
④《管子·五辅》。
⑤《苟子·君道》。
⑥张锡勤、柴文华:《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上卷),人民出
版社,2008年,第138—139页。
⑦《孝经·开宗明义章》。
⑧《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
与展望》,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第48页。
⑩《吕氏春秋·孝行》。
⑥潘光旦:《论“对民族行其大孝”》,载潘光旦《寻求中国人位
育之道——潘光旦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
423页。
⑥黄修明:《中国古代“孝治天下”的历史反思》,《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4期。
⑩《南齐书》卷二十一《文惠太子列传》。
作者简介:王健崭,哲学博士,中国药科大学
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在职博士后。
南京,21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