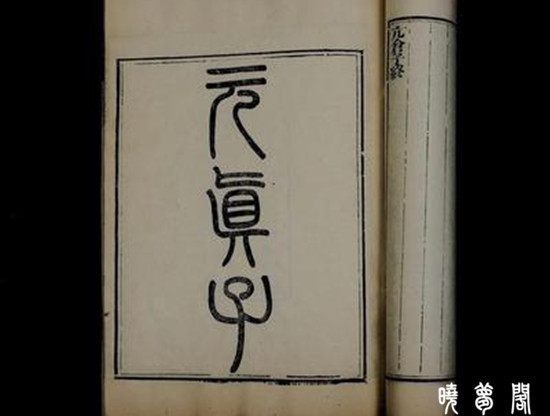论坛介绍
佛教文化与“非遗"
王月清,雒少锋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渐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上,佛教高僧大德及广大信众契理契机地创造了既阐扬佛门义理又弘传中华价值观的佛教文化形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虽然历经时代变迁,却因其具备独特性而成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内容,以及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涵养资源和重要载体。这里谨就佛教文化在“非遗”保护中的特殊性以及保护中涉及的问题作一番思考和探讨。
一、佛教“非遗”的划界与特质
就目前的“非遗”项目来看,我们应该首先对涉佛“非遗”与佛教“非遗”两种项目有所区分。前者指“非遗”项目的内容或形式与佛教关联,但其本身可以独立存在,而不必隶属于佛教。比如金陵刻经处乃佛教居士杨仁山所创,并以刻印佛教经典为主,但在将其作为“非遗”项目时,主要是为了保存活态的中国古代传统的木刻水印技术,因此,金陵刻经的印刷技艺应隶属于“民间技艺”品目,而其与佛教之间的关联仅在于印刷内容,故而应属于涉佛“非遗”。此外,这类项目还包括那些非佛教人士所创造的文艺作品,如达摩传说、《鱼篮观音宝卷》等①。这些作品只是借用了佛教的某些元素,但整个故事叙事和传播与正统佛教的意趣有较大距离,属于涉及佛教而非隶属于佛教。真正的佛教“菲遗”项目,其形式和内容均与佛教有关,比如佛教音乐、佛教节俗等。就两种项目的应用范围来说,涉佛“非遗”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指称,可以包含后者。在这里,为了从相对宽泛的视野考察佛教与“非遗”保护的关联,我们以涉佛“非遗”这个名称指代“非遗”名录中所有与佛教关联的项目。一般而言,“非遗”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包括活态性、可传承性、地域性和社区性、教喻性和期望性等,但佛教在这些方面有着更为特殊之处。如在可传承性方面,由于佛教团体千年来以较为稳定的形式传承,故而佛教团体的技艺一般较之其它民间手工技艺具有更为强盛的生命力。此外,在教喻性和期望性方面,佛教在历史上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教化民众的方便法门,现今所传的不少“非遗”项目都体现出了此点。此外,佛教“非遗”还表现出其它“非遗”项目所不具备的特质,以下从三个方面予以阐明。
1.中国元素。佛教最初由印度传人,其后在中土发扬光大。因此,在论及涉佛“非遗”项目时,首先需要确认其中哪些属于中国元素,唯其如此,才能体现中国佛教“非遗”项目保护传承之价值所在,这也是佛教“非遗”与其它“非遗”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从中国现有的涉佛“非遗”项目来看,绝大多数属于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内容,佛教只是问接借用的元素,而即便在较为纯正的佛教“非遗”中,也主要体现的是中国元素。比如最具印度色彩的佛教梵呗,尽管最初传自印度,且在三国两晋时期已有支谦、康僧会、帛尸梨蜜多罗等胡僧创作梵呗,但这些西域僧人所制的梵呗并未广泛流传,中国后世所传梵呗都是基于三国时期曹植所创的“鱼山梵呗”,故历史上尊称曹植为中国梵呗之始祖。正是由于这一项目的发明权是中国人,故“鱼山梵呗”也成为我国第二批国家级“非遗”项目。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在批准涉佛“非遗”时,已经充分考虑到凸显中国元素的重要性。
2.民间色彩。在佛教流传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精英佛教与民问佛教的区分。精英佛教重在追求人生的终极解脱,并且专注于佛教所提倡的禅修和教理讨论;而民间佛教则重在祈求现世来世的福报,并以礼佛念佛为主要信仰活动。这两种不同的需求产生了不同的佛教文化形式,前者多以注释佛教经典的文字文献形式存在,这也是现代佛学研究的重要资源;后者则只是作为佛教信仰活动的一部分,较少有官方记载存世。但实际上,目前的涉佛“非遗”名录却更多地涉及后一方面。我们认为,民间的涉佛“非遗”项目亟需得到保护和传承,因为在时代的变迁中,民间佛教有渐行渐远乃至消失的危险,同时,其存在的形式往往具有地方和时代的烙印,因此也更应成为“非遗”关注的重点
3.信仰内核。宗教类“非遗”与非宗教类“非遗”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即宗教类项目一般都局限在宗教场所,并由相应的教职人员演绎,如金山寺的水陆法会音乐即在寺院内由僧人按照传统方式演奏,这就对佛教“非遗”传承人的身份有所限制,即必须是佛教信徒,而非宗教类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却可以更加开放。但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有些涉佛“非遗”项目只是与佛教关联,而其保护的并非佛教的内容,比如雕版印刷术,既可以印刷佛教文献也可以印刷其它内容,其传承人也不必是佛教徒。如果以此来推理,“非遗”保护的主要是文学、节日、民俗这类形式,那么像金山寺的水陆法会音乐似乎也就没有必要仅限于出家人演奏,但倘若如此,恐怕就不是真正的水陆法会了。这就提示我们注意,佛教“非遗”的保护不仅要注重形式,而且要尊重信仰本身。这种内在的信仰与外在的形式有着严格区别,内在精神信仰、伦理教喻、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决定了外在形式,“非遗”文化形式、“非遗”技艺背后的传承创造的主体应当是荷担思想信念的主体,应当是对信仰和义理有同情之了解的主体。据此我们认为,涉佛“非遗”项目的保护,必然只能由佛教信仰者传承,这里的信仰者不仅是信仰三宝的僧人,也包括那些参与法会的民众,双方必须都信任自己所面对的法会内容,而不是将法会音乐只是看作艺术表演。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教“非遗”保护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保持某些形式,更重要的是保持信仰的本真和纯正。
二、佛教“非遗”的研究与传承
目前,“非遗”保护是从学术研究和保护实践两方面进行的,在佛教“非遗”保护中同样也是如此。由于“非遗”尚属新兴的研究领域,在保护实践和学术研究上还有诸多可深入之处,在此我们拟就学术研究本身如何更好地服务于“非遗”保护等问题加以探讨。1.多学科的综合。当前的佛学研究以思想研究为主阵地,关涉佛教“非遗”时,其中有对佛教图像、造型艺术等佛教文化艺术的考察,但后者往往为艺术学或民俗学所关注。邢东风曾就此提出批评,认为在佛教“非遗”的领域需要相对减少佛教义理方面的研究,“使更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更多地提倡和鼓励实证性的微观研究,自觉地把实物资料纳入研究的视野,这样不仅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扎实、更具体,而且可以为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具有直接参考价值的成果,也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佛教文化遗产的认识”①。他甚至认为,那些义理的研究对于佛教“非遗”的确认、研究和申报来说毫无用处。邢东风的批评当然是针对佛教“非遗”研究来说,他所说的义理研究对于“非遗”研究不适用的方面其实也呼应了上文提及的佛教“非遗”中民间佛教与精英佛教的区分,因而与其说现代的佛教义理研究不适用于“非遗”,不如说是目前“非遗”的研究目标一开始就确定在了民间佛教的层面,从而造成二者的错位。那么是否为了研究佛教“非遗”,应该建立另一种专门投入到田野调查中的佛学研究队伍呢?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因为“非遗”并不存在专门的研究方法,可以从不同学科角度切入,且佛教“非遗”研究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更应对每个可能的学科开放,并围绕“非遗”保护的共同目标,逐步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机制。这种多学科协同研究的好处是,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可以完全从自己的学科专长出发,整合发挥各自学科的独特优势。我们没有必要苛求一个佛教义理研究者一定要亲身去做田野调查,他完全可以与专业的人类学或社会学人士合作。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展各自的工作时,可按照一个总的目标建立某种相互促进的关联,最终使得研究成果融为一体。当然,这一协同研究机制的建立需要调动较多的资源,操作难度也相对较大,但是一旦建立,其效用则要比目前散兵游勇式的研究更为高效。这是未来佛教“非遗”研究中值得尝试的路径。当然,这种多学科的交叉、合作,最终除了带来研究组织方式的变革外,更多的应是研究者主体的多学科视角和眼光的增进,以及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加强。
2.契理契机的保护。“非遗”保护的要义之一在于保持“非遗”对象的本真性,尽可能使其不走样、不变形。但是对“非遗”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是否也只限于此呢?或者说,对“非遗”的学术研究除了更好地确认“非遗”项目以及为其保护提供相应的对策,是否还有其它建设性作用呢?无论目前学界对“非遗”研究的学术目标如何界定,人们都会期待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在原地不动地叙说,而是能够创造新的文化形态或社会效应,而这一期待也能够为“非遗”保护提供新的理路。以佛教“非遗”来说,通常人们关注的只是其形式,而实际上其中有大量有关文学、音乐、节日、仪式等等方面的内容。比如河西宝卷、吴地宝卷中蕴含着丰富的佛教故事,其中多有化世导俗之类的伦理教化内容,此属于佛门劝善书的范围①。这些文学形式在一个地区广泛流传,说明这些故事颇为契合当地百姓的生活和精神需求。如果将劝善书中的劝善故事和基本思路改编为小说、戏剧影视、动画等多种现代艺术作品,对现代道德建设当不无裨益。此外,透过专业性的学术研究和创新的“非遗”劝善文化,还可对治目前一些地方直接将“非遗”项目商业化的困境,因为那种直接借用“非遗”项目营利的做法,必然会为迎合市场的需求而损害“非遗”对象的某些特质,从而丧失“非遗”保护的意义。我们认为,尊重“非遗”的本真性和价值理性的现代创作和现代化运营才是契理契机的正道,所以在保护和开发利用之间,公益追求、价值追求是最重要的。
3.主客交融的传承。涉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理想的样态应是现代情境下的主客交融而非使保护对象成为没有现代生命的孤立的客体,以及使传承人成为技道分离的孤立的主体。在涉佛“非遗”项目的传承中,比较突出的是信仰和地域性问题。信仰的问题上文已经有所提及,地域性则是指项目的传承与某一地区密切关联,离开特殊环境便不能存在。比如江苏靖江讲经使用的是当地方言,这就要求传承人与受众都需懂得这一语言,如果离开这种语言,那么就不再是靖江讲经了。因而,“非遗”的保护不能局限在项目本身,而要首先尽力保护其关涉到的外围环境,唯其如此,才能使“非遗”本身获得良好的传承延续。但是这种超出“非遗”项目之外的保护显然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或其它力量,而需要传承人所在的群体积极参与其中。涉佛“非遗”项目一般都有一定的信仰基础,而能够传承“非遗”项目的人也应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这就与对一般“非遗”项目传承人的要求有所不同。佛教的“非遗”传承人可以借助信仰优势影响公众,从而有益于“非遗”外部环境的营造。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的,信仰的真实源于民众情感的真实,而能够起到推助和引导作用的,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传承人的修持和操守。这就要求佛教“非遗”的传承人不仅要熟悉项目的技艺,而且要具有高尚的德行,以达到知行合一的传承。
3.主客交融的传承。涉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理想的样态应是现代情境下的主客交融而非使保护对象成为没有现代生命的孤立的客体,以及使传承人成为技道分离的孤立的主体。在涉佛“非遗”项目的传承中,比较突出的是信仰和地域性问题。信仰的问题上文已经有所提及,地域性则是指项目的传承与某一地区密切关联,离开特殊环境便不能存在。比如江苏靖江讲经使用的是当地方言,这就要求传承人与受众都需懂得这一语言,如果离开这种语言,那么就不再是靖江讲经了。因而,“非遗”的保护不能局限在项目本身,而要首先尽力保护其关涉到的外围环境,唯其如此,才能使“非遗”本身获得良好的传承延续。但是这种超出“非遗”项目之外的保护显然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或其它力量,而需要传承人所在的群体积极参与其中。涉佛“非遗”项目一般都有一定的信仰基础,而能够传承“非遗”项目的人也应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这就与对一般“非遗”项目传承人的要求有所不同。佛教的“非遗”传承人可以借助信仰优势影响公众,从而有益于“非遗”外部环境的营造。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的,信仰的真实源于民众情感的真实,而能够起到推助和引导作用的,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传承人的修持和操守。这就要求佛教“非遗”的传承人不仅要熟悉项目的技艺,而且要具有高尚的德行,以达到知行合一的传承。
更多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