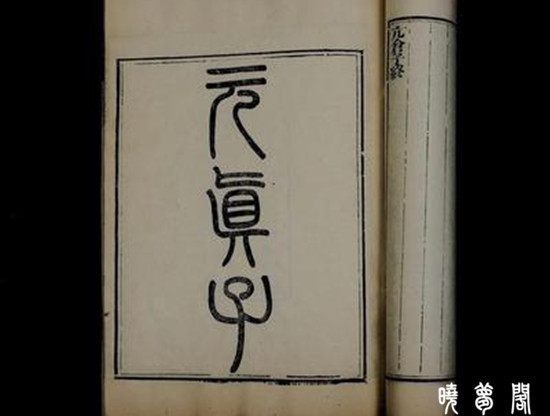周苇风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
王逸《离骚叙》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 虬龙鸾风,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在此对《离骚》中的比兴意象进行了综合分析,虽然主要是针对《离骚》一篇而言,实可视为对全部楚辞作品的意象群落的高度总结。
屈原在《离骚》中说:“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皆然。”屈原自比鸷鸟,按说鸷鸟应该属于善鸟一类。然而《说文·鸟部》云:“鸷,击杀鸟也。”鸷鸟既然是凶猛的鸟,在意象群的归属上似乎又不应该属于善鸟一类。王逸《楚辞章句》:“鸷,执也。谓能执服众鸟,鹰鹳之类,以喻中正。”对王逸的解释,姜亮夫先生表示不能理解,理由就是执伏众鸟,则其不群,乃为凶残,不为忠贞矣。鸷鸟该怎样解释?姜先生的《屈原赋校注》认为,鸷乃执之讹,执、挚为古今字。挚者,诚信忠贞之义…。在姜亮夫先生看来,王逸以鸷鸟喻中正是不错的,但不应该释鸷鸟为猛禽。
笔者以为,鸷鸟确乎是猛禽,但同时也是屈原心目中的“善鸟”。那么,如何解释屈原将执伏众鸟、貌似“凶残”的鸷鸟视为“善鸟”这种文化现象呢?从现代文学批评的观念来考察和分析,笔者以为可以用“原型意象”来加以说明:《离骚》“鸷鸟”意象的原型是东夷少嗥部族崇拜的飞鸟,在楚人观念中凤鸟具有鸷鸟的部分属性。
一
原型批评是盛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种批评模式,它将现代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努力透过文学现象去探索深层的原型内涵,并进一步分析文学与神话传说、宗教仪式等原始文化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内在规律。原型批评的理论核心是原型,它往往指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经典意象,可以是主题、人物,也可以是情节结构模式,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反映。人类的许多集体无意识源自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进人文明社会后,尽管先民对图腾崇拜的记忆逐渐朦胧暗淡,但图腾崇拜所形成的原始意象依然制约着社会的精神生产,并作为遗产信息发挥着重要作用。楚辞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早期代表,它的创作也借助于原始图腾的力量,保留了原始图腾的痕迹。
楚辞作品中出现最多的是螭龙和飞鸟形象,尤其是乘龙驾风最为引人注目,并且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系统中最基本的形式化单位,在文学史上不断重复出现。楚辞作品中,龙凤形象的象征性及其内涵,很大程度上是由龙风自身特点决定的。也就是说,楚辞作品中的龙凤形象已经脱离了原始图腾阶段,获得了独立地位,是一个新的原型。
中国历史上的图腾对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鸟类,如凤、燕;兽类,如虎、熊;六畜类,如犬、马、羊、猪;虫类,如蛇、龙;水族类,如鱼、龟。上述五类中,鸟类和虫类图腾的影响最为深远,人类至今常常龙凤并提。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凤图腾源于东夷的少嗥氏。春秋时期郯国的君主是少睥后裔,《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其云:“我高祖少嗥挚之立也,风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少嗥氏以鸟名称呼各种官职,把飞鸟作为图腾对象,凤鸟氏是其总管(鸟图腾源于东夷,在学术界已成定论,没有什么疑问。对于龙蛇图腾的发源地点,解说颇为歧义。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龙蛇图腾起源于西部华夏部族,随着部族的融合而成为各地区先民共同的图腾旗帜。李炳海先生则认为,龙蛇图腾也是源于东夷,从太嗥集团那里首先兴起旧J。太嗥又称伏羲,风姓。《说文》:“风,八风也……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从虫,凡声。”从文字学的角度看,繁写的风(凰)在形体上从虫,虫指的是龙蛇之属。太嗥伏羲发祥于东部地区,传说华胥在雷泽履大迹而生伏羲。关于雷泽的具体地点,或说在山东鄄城境内,或断定就是今日的太湖,总之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山海经·海外南经》载:“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郝懿行注:“今东齐人亦呼蛇为虫。”东南沿海地区呼蛇为虫,那正是太嗥的发祥地。由此证明,太嗥风姓,从虫,就是说太嗥蛇生,实际是以蛇为图腾
对象。古代典籍多言伏羲人首蛇身,如《艺文类聚》卷1l引《帝王世纪》:“太吴帝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庖牺即伏羲。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砖墓画像中的伏羲、女娲形象,腰身以上是人形,穿袍戴冠,腰身以下则是蛇躯,尾端亲密地卷曲在一起。又山东嘉祥汉代武梁祠西壁画像石,伏羲、女娲的形象亦同于南阳汉墓画像,伏羲在左,手执曲尺,女娲在右,手执圆规,他们中间有一小孩,双脚如尾。至于后来的龙图腾,则是蛇图腾的延续和升华。
楚人源自何方,说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楚民族来自东方。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根据自己对《令簋》、《禽簋》等西周铭文的研究,
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为殷之同盟国。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进一步论述,说“淮夷即楚人,亦即《逸周书·作雒解》中之‘熊盈族”’【6],又在《金文丛考》一书中说:“楚之先实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门1胡厚宣在其《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也指出,楚是来自东方鲁地的民族。后来,随着周民族的向东扩展以及黄河流域气候的逐渐改变,东方民族大多南迁,其中以楚民族势力最强,以后便发展到南方的江汉流域旧J。东夷的具体分布,据傅斯年研究,在“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L9 J。而那里也曾是楚人旧居。巫山是楚境内的名山,据古典文献记载,山东境内也有巫山。《左传》襄公十八年:“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杨伯峻注:“巫山在今山东肥城县西北六十里。”古族搬迁往往携带地名同行,例多,不烦举。《左传》隐公七年、僖公二年皆言及楚丘,一为卫地,一在曹县东南,皆东方之地。《左传》之楚丘,或为楚之废墟。西周时,楚国蜗居于荆山、雎山之间。春秋时期不但囊括了荆楚大地,而且出方城,与齐晋争霸中原。战国时期,楚国疆域进一步扩张,西北到今陕西东南部,西南到今广西东北部,东北到今山东南部。《史记·货殖列传》:“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为南楚。”楚人再次与东夷后裔混居在一起。楚人与东夷族在历史上存在着密切关系,楚辞作品中的螭龙和飞鸟形象应该就是东夷族龙凤图腾所投下的影像。
当我们的祖先即将跨人文明的门槛时,战争一场接一场地来到。先是阪泉之战,整合了华夏部族内的秩序。接着就是涿鹿之战,确立了华夏族群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主体地位。紧跟着,尧、舜、禹三代都先后对长江流域的苗蛮部族发动过战争,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更向南方。这几场战争,代表了黄河流域各部族之间及黄河流域的主体族群与东夷族之间的文化撞击。文化的渗透与权力的支配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一个被打败的部落或氏族可以从此听从打败他的部落的支配,但征服者绝不可能彻底消除被征服者的文化和信仰。《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成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显然,蚩尤虽被杀,但在东夷故地的强大影响力仍然存在,也受到了黄帝——这个对手的尊敬。它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应为涿鹿之战后,华夏、东夷两大部族集团融合的趋势加强了。这种融合,除血缘的族裔的元素外,毫无疑问地,还包纳了文化的因子。华夏部族的龙风意识可能就是经历涿鹿之战后东夷部族的图腾意识渗透到华夏部族中去的结果。
东夷族龙凤图腾在初始阶段构成的神话形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原始意象或原型,在渗透外族文化的过程中不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无论是楚人还是华夏族,在移植东夷族的龙凤图腾时,都会按照本民族的审美观念和心理需求进行一番改造。许多图腾崇拜源自人们对图腾对象的恐惧,由恐惧产生敬畏,进而导致崇拜。因此在文献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矛盾的记载,一方面图腾对象被视为人类的保护神,另一方面又是噬人害人的猛兽、怪物。龙的原型或说是蛇,或说是鳄鱼等等。蛇、鳄鱼在上古对人类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至今仍使人不寒而栗。龙是这样,凤也如此。《淮南子·本经训》载后羿射日故事,其中讲到“禊输、凿齿、九婴、大风、封稀、修蛇,皆为民害”,后羿上射十日,下杀禊输,“缴大风于青丘之泽”。先秦风、凤二字相通,“大风”即大凤。又《览冥训》载女娲补天时曾言“鸷鸟攫老弱”,其中鸷鸟或即后羿所射之“大风”。后羿射目发生在帝尧时候,断修蛇、射大风折射出华夏部族与东夷部族斗争的历史影像,同时也可见出龙凤原始意象的粗蛮和鄙恶。但在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中,龙风呈祥是很好看的一种。画面上,龙、凤各居一半。龙是升龙,张口旋身,回首望风;风是翔凤,展翅翘尾,举目眺龙。周围瑞云朵朵,一派祥和之气。龙是男性象征,充满了阳刚之气;凤是女性象征,充满了阴柔之美。龙渐渐隐去了令人恐惧的一面,凤也完全没有了鸷鸟的朴拙与野性。
中原各国没有龙凤相斗的传说。《韩非子·十过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风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腾蛇伏地,凤皇覆上”,这本来是战争的场景,在韩非子的笔下却变成了和平的图画。在楚人的艺术作品中,龙凤相斗却是屡见不鲜的题材。据张正明先生《楚文化史》言:“(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已见刺绣纹样十八幅,其中风与龙俱出的十幅,有凤无龙的七幅,有龙无凤的一幅。在凤与龙俱出的刺绣纹样十幅中,凤与龙互斗的八幅,凤与龙相安无事的二幅。在凤与龙互斗的刺绣纹样八幅中,风进龙退、凤胜龙败的五幅,势均力敌的三幅。”引楚俗尊凤,战国时代的楚人把一切美好的特性和特征都赋予了凤,而对龙却带几分恶感。究其原因。张正明先生认为或与吴越曾是楚人劲敌,偏偏吴越都以龙为图腾有关。楚国出土的龙凤相斗文物,凤胜龙败,就是这种现实的斗争意识的反映。后越灭吴,楚灭越,及至战国中期,吴越故地成为楚国郡县,龙对楚人已失去威胁作用,加上受中原各国好龙风气的影响,于是楚人对龙又爱又恨。刘向《新序·杂事》有叶公好龙的故事。叶,春秋楚邑名。叶公好龙的故事最能反映楚人对龙的复杂心理。在楚人刺绣纹样中,龙也是壮美的,然而通常只能担当陪衬甚至反衬的角色。
三
在出土的楚国文物中,凤的雕像和图像多得不可胜数,仅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木胎漆绘凤雕像就有36件(虎座鸟架鼓每座有凤两只,按两件计)。楚地出土的战国丝织品和刺绣品的花纹,在动物纹类中,凤纹特多。楚人好以凤喻己或以凤喻人。《庄子·秋水》:“南方有鸟,其名鹪鹤,子知之乎?夫鹌鹅,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鹪鹞乃凤属,是以凤喻己。《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凤兮,凤兮,何德之衰。”’是以凤喻孔子。在屈原的作品中,曾多次将鸾凤引入他所营造的世界中,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赋予了其高尚、圣洁、优雅、超逸的人格品质。在《涉江》一诗中更对鸾风寄予了绵绵深情:“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将凤鸟意象进行理想的人格化,是屈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的一大贡献,由此引发后世贤哲每每将凤与龙并称以称颂人中精英。
少嗥氏以飞鸟为图腾,凤只居其一,其也还有玄鸟、青鸟、丹鸟等等。东夷族有玄鸟生商的神话,玄鸟即燕子。东夷族崇拜太阳,太阳中传说有三足乌。许慎《说文解字》卷4亦云:“凤,神鸟也。天老日:凤之像也,麟前鹿后,蛇颈鱼尾,龙纹龟背,燕额鸟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受东夷文化影
响,楚人的凤鸟形象在当时也不固定,“又象雉,又象鹑,又象跋乌”。楚地出土的木胎漆绘凤雕像,“形体特征怪异,曾因颈足俱长而被误认为鹭鸶,因钩喙而被误认为鹰,在更多场合下则被笼而统之称为鸟了。风的原型是哪种鸟,现在谁也说不准了”。江陵雨台山166号墓出土的虎座立风¨引,首、颈、身、足分雕合装,除了两只翅膀外,又多插了两只鹿角。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三头风纹绣》引,形象更为怪异,凤首如枭,双翼对举,两个翼端都内勾如风首。从三头凤怒目如枭、鼓腹近圆的形象可以看到,枭也曾经是凤的形象的一部分。
安徽寿县出土的《攫蛇铜鹰》。鹰作盘旋状,双翅张开,双腿粗壮,夸张地攫住一条盘曲的长蛇。其实,将此件出土文物命名为《攫蛇铜鹰》未必确切。蛇即龙,一物而异名,鹰其实就是凤。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风斗龙虎纹绣》引,在一件绣罗单衣上,可以看到由一凤斗二龙一虎为一个单元的刺绣纹样。凤一足后登,作腾跃状;另足前伸,方攫下部一龙之颈,此龙逃窜,作痛苦状。凤一翅击中上部一龙之腰,此龙遁走,仰首张口作哀号状;凤另一翅击中前方一虎之腰,此虎亦仰首作哀号状。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中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郭沫若先生认为,帛画表现的是象征生命与和平的凤鸟同象征死亡与战争的夔龙正在搏斗,帛画中合掌的妇人在祝贺风鸟取得胜利。安徽寿县出土的《攫蛇铜鹰》,想必作者曾经从鹰蛇相斗的自然现象中得到启示。但就它的构思来说,其创作意图与《凤斗龙虎纹绣》和《人物龙凤帛画》当无二致,即表现龙凤相斗,凤胜龙败。
在楚入观念中,凤带有鹰的特征和特性,枭曾经是凤的形象的一部分,隐约透露出凤的意象原型的粗野和可怕,反映了先民对凤鸟恐惧与敬畏的原始心理。正是凤鸟具有鸷鸟特性,使得楚入之凤具有了无与伦比的力量和一往无前的勇气,保证了凤在与龙的争斗中能够最终胜出。
凤体庞大,当然不易合群。鹪鹳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正是凤之个性的流露。《说文·鸟部》:“鹏,古文凤,象形,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许慎之说盖非楚人之凤。《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群即合群。风之合群乃北方儒家观念的反映,是北方西周大一统的产物。而楚国,远在化外,《史记·楚世家》载熊渠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显示了楚人特立独行的个性精神。
《史记·楚世家》载伍举谏楚庄王日:“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日:“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庄王自比于冲天惊人之鸟,什么样的鸟有如此气势?观出土的楚国文物,联系庄子笔下的大鹏,是鸟非凤鸟莫属。庄王的冲天而鸣,庄子笔下的大鹏扶摇而上,俱是出群之举。在哲学上,老子讲小国寡民,讲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庄子讲相忘于江湖,讲曳尾涂中,都与北方的合群观念大相径庭。
据统计,《离骚》一诗用“余”49次,用“吾”26次,用“朕”四次,用“予”四次,其中只有“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三处分别为女委詈词和灵氛占词,其中的余、予不是屈原自指。屈原是我国第一位独立歌唱的伟大诗人,《离骚》是屈原极富个性的政治抒情诗,不断提及自我本不足为怪,但也由此反映出屈原强烈的自我意识。屈原的作品主要在围绕自己的忧愤说事,《离骚》中有大段自我赞美的段落。屈原在作品中喋喋不休地反复吟咏自己的行动和心情,以至有人认为“读之令人觉得也未免太有些自吹自擂”。在《离骚》中,主人公披花饰草,缠绵悱恻。为了表现自己的高大巍峨,《离骚》将昏君佞臣与“我”并置对照,以此将自己置于美丽、孤危、哀怨的境地进行描述,突出自己的美丽、孤独和清高。屈原这样写,其目的无非是说自己与众不同,独立不群。
在《离骚》一开始屈原就宣称自己:“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
则兮,字余日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炫耀自己高贵的出身,不凡的生辰,高洁的品质,远大的志向。对自己内美与外美的过度自信,使
屈原在楚国找不到一个知音。屈原借女耍之口批判“世并举而好朋”,他自己也深以“竞周容以为度”为耻。他甚至在《渔父》中声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将自己置于众人的对立面。春秋时期有所谓的“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不朽的途径有三条,即立德、立功、立言。在三不朽中,屈原更看重立德。寄意怀王,实行美政,表面上是为了立功,但他处处以三后美德约束今王,立功实际上成为屈原道德完善的一个手段。因此,他鄙视众人的竞进与追逐,固守着自己“恐修名之不立”的信念。战国时期,纵横家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争名夺利,对传统道德造成了极大冲击。苏秦认为信、廉、孝不过是“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苏秦所谓的进取,实际即追名逐利,是屈原竭力反对的。屈原自比鸷鸟,以大凤无与伦比的勇气站在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对立面。
综上所述,楚辞作品中的螭龙和飞鸟形象是东夷族龙凤图腾所投下的影像。楚人在移植东夷族的龙凤图腾时,按照本民族的审美观念和心理需求进行了一番改造,把一切美好的特性和特征都赋予了凤,而对龙则又爱又恨。鹰、枭俱为猛禽,都属鸷鸟一类,楚人之凤具有鹰、枭的某些特点,隐约透露出凤鸟意象原型的粗野和可怕,反映了先民对凤鸟图腾恐惧与敬畏的原始心理。凤在楚人观念中孔武有力,硕大健壮,是力量和勇气的化身。从原始图腾的崇拜心理和楚人对凤之形象的建构不难理解屈原何以自比鸷鸟。屈原以鸷鸟自比,独立不群,从凤鸟身上汲取了无穷的力量和勇气。
参考文献:
[1]姜亮夫.屈原赋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38.
[2]李炳海.楚辞与东夷族的龙凤图腾[J]求索,1992(5).
[3]南阳文物研究所.南阳汉代画像砖[M].北京:文物出版
社。1990.
[4]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
社.1986.
[5]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263.
[6]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46.
[7】鄣沫若.金文丛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44.
[8]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M]∥史学论丛:第一册.北
京:北京大学潜社,1934.
[9]傅斯年.夷夏东西说[M]∥史料论略及其他.沈阳:辽宁
教育出版社,1997:165—166.
【10]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178.
[11]荆州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0
(5).
[12】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178.
[13]张正明.巫、道、骚与艺术[J].文艺研究,1992(2).
[14]张正明,腾壬生,张胜琳:凤斗龙虎图像考释[J].江汉
考古,1984(1).
[15]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14.
[16]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178.
[17]皮道坚.楚艺术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268.
[18]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14.
[19]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J].人民文学,1953
(11).
[20]冈村繁:楚辞与屈原[M]∥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
丛:第一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1